文/謝璦竹
人類是社會的動物,有同理心,會互相幫忙,但人類卻也會彼此爭鬥,小至校園霸凌,大至國家民族間的戰爭。從神經科學來看,這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最新的社會神經學實驗發現,當別人受苦時,我們大腦中的疼痛網路會活化,也就是說,看到別人遭受痛苦,與自己遭受痛苦,兩種情形使用同樣的神經機制,這就是同理心的基礎,也是我們看電影時,會跟著情節又哭又笑的原因。
美國神經科學家伊葛門(David Eagleman)在他的《大腦解密手冊》裡解釋,這種感受別人痛苦的內建能力,從演化的觀點看,可以讓我們更容易經由掌握別人的感受,進而準確預測他們的下一步行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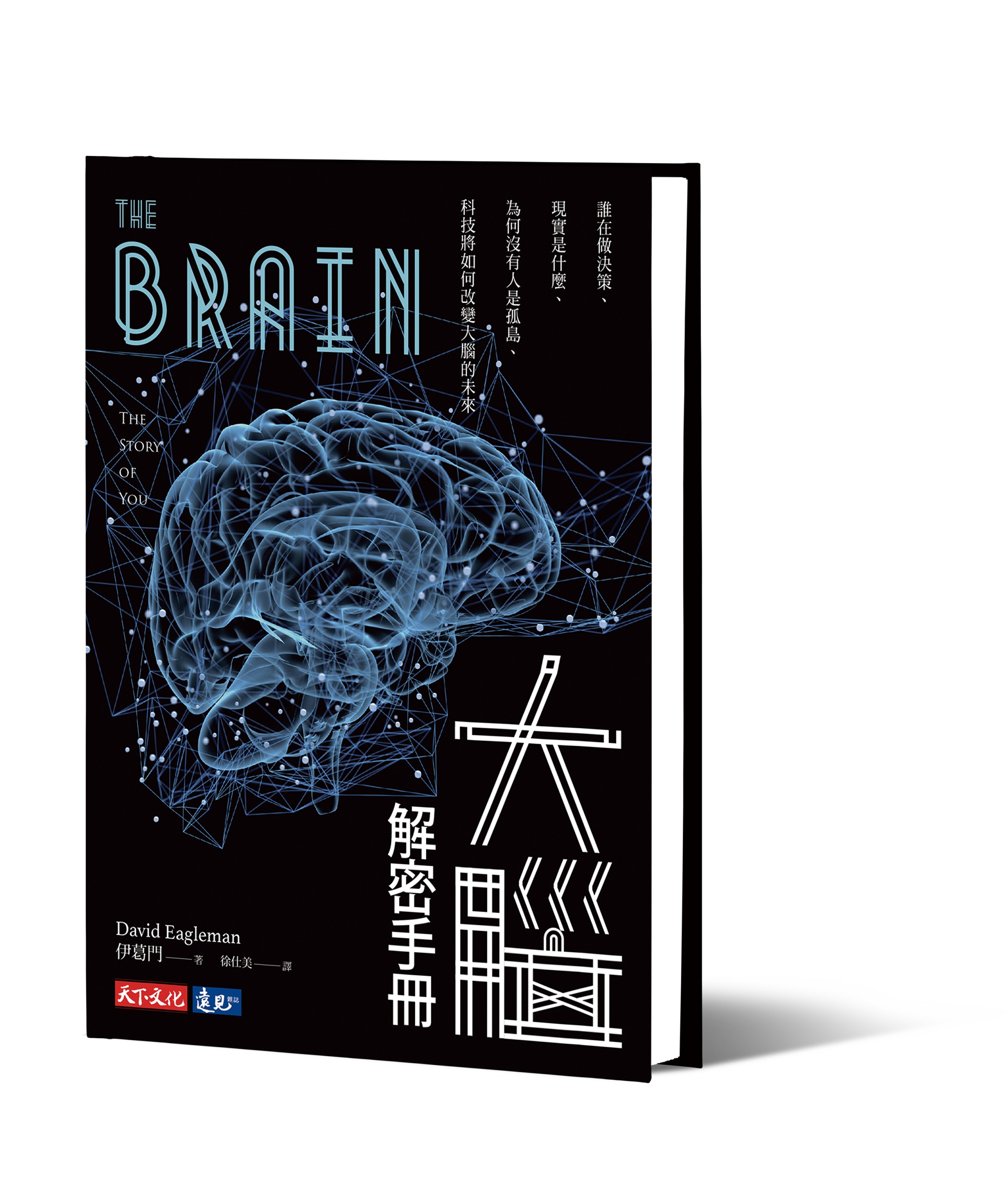
為了更能夠掌握別人的感受,我們還會自動模仿別人的表情。作者做了一個實驗,讓人們看一組臉孔的照片,並觀察他們臉頰與額頭的電活動。當看到微笑或皺眉的照片,可以測量到短期的電活動,這些活動很細微,我們自己往往並不知覺,但這是一種稱為「鏡像」的現象,參與者自動用臉部肌肉模仿看到的表情,就像照鏡子一樣。作者解釋,這也是為什麼結婚很久的夫妻常會有「夫妻臉」,就是因為他們多年來像照鏡子似地看著對方、模仿對方,使得兩人連皺紋的紋路也愈來愈相似。
人人有同理心
作者進一步實驗,給兩組人看一組臉孔照片,請他們選出最能形容該表情的一個詞。其中一組施打了肉毒桿菌,肉毒桿菌常用在美容醫學,目的是透過肌肉麻痺,減少皺紋。結果發現,施打了肉毒桿菌的那組,判讀照片中情緒的表現比較差。作者認為,這說明了缺少來自臉部肌肉的回饋,使我們解讀他人情緒的能力變差了。
大腦的疼痛網路不僅僅只有在自己或別人遭受身體上的疼痛時才活化,當我們感覺到社交排斥時,也會活化疼痛網路。神經科學家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設計了一個實驗,受試者玩一個拋接球的電腦遊戲,遊戲中另外有兩個人,這兩個人實際是由電腦程式操作的,但受試者以為那是由另外兩個真人所控制。
起初,三個人一起玩拋接球,後來電腦程式操控的兩個玩家開始彼此拋接球,把受試者排除在遊戲外;結果顯示,當遭到排擠時,受試者的疼痛網路也會開始活化。這種社交需求會讓我們透過家庭、友誼、工作、風格、運動、宗教、膚色、語言文化或政治立場的關係,凝聚在一起,產生了歸屬感。
然而,歸屬感會不會使我們對團體外的人進行排擠呢?伊葛門的實驗發現,對人的同理心,的確會因為對方與自己是不是同一團體而不同。
他讓受試者看螢幕上手被針戳到的影片,正如前述,當看到別人痛苦時,我們大腦中的疼痛網路也會活化起來。接著,他給六隻手分別標上文字,分別是「基督徒」、「猶太教徒」、「無神論者」、「穆斯林」、「印度教徒」與「山達基教徒」等,再讓受試者隨機選擇一隻手,觀看手被針戳到或棉花棒碰觸的影片。
同理心未臻平等心
結果發現,如果看到的是與自己同樣信仰(或同樣無神論)的內團體的手受苦時,腦的同理心反應比較大;反之,則比較小。
實驗結果很值得深思,因為這僅僅是文字標示而已,就會使大腦產生不同的反應。伊葛門也指出,無神論者對於標示「無神論者」的手,反應也會比較大,這顯示該結果與宗教無關,而是與所屬的團體有關。
研究者想要由此探討不同團體、族群之間的對立、敵視的態度。若僅僅如上述只是同理心少一些,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種族歧視所引發的暴力行為。
事實上,種族歧視也好,校園霸凌也好,甚至疫情期間,曾有新聞報導,有人拿酒精水球丟向流浪漢,這些情形天天都在我們身邊發生。也許選舉期間會特別有感覺:藍綠不同陣營的支持者,壁壘分明,常常連一家人也會因此吵得面紅耳赤,只因為政治立場不同;更不用說本來就不是一家人的朋友或陌生人間,僅僅由於支持對象不同,我們就會戴上有色眼鏡去檢查他的言行,而無法平心靜氣聽對方說話。
上述手上貼了宗教屬性文字標示的實驗,就鮮明地呈現了什麼叫做「貼標籤」,一旦一個人被貼上標籤,我們看待他就難免有成見,進而影響我們對待他的方式,而這些都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

禪宗第八十五代宗師悟覺妙天禪師常說,「平常心,心常平」。什麼是平常心?就是一切平等、無分別的心。從神經科學來看,我們的前額葉某些部分是涉及抽象思考、計劃未來、專注於個人自我感。經過長期訓練的運動員,可以進入所謂「心流」的狀態,就是在不受上述前額葉背景「聲音」干擾的情況下,完全依賴長年全心訓練而刻入腦中硬體的運動技巧,可見意識有時候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是一種干擾。
意識也不等於所謂的自由意志,意識只是潛意識的冰山一角。我們常會發生說錯話後悔的情形,就是因為在意念形成之前,我們的潛意識在幾個小時前、甚至幾個月前,就一直努力塑造那些意念,包括鞏固記憶、試驗新組合,以及評估後果。
潛意識有一個功能,就是「內隱式自我膨脹」(implicit egotism),也就是容易讓我們聯想到自己的事物,對我們特別有吸引力。舉例來說,一張合照中,我們一定先看自己。
不僅如此,有一個有趣的統計,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佩蘭(Brett Pelham)分析了牙醫學院和法學院的畢業生紀錄,發現名叫Dennis或Denise的牙醫(dentist)及名叫Laura或Laurence的律師(lawyer)特別多。由此可見,要做到「平常心、心常平」,的確需要付出努力。
就是因為人類大腦先天就有這種「不平等」的功能,因此我們先天的同理心也有限制,會自動區別內團體與外團體,而給予不同的對待。
大腦會「去人性化」
荷蘭萊登大學的哈里斯做過一系列實驗,發現大腦內側前額葉皮質,在我們想到其他人的時候會活化,但涉及無生命物體時,好比咖啡杯,該腦區不會活化,因此是腦中的社交網路。他請受試者觀看不同族群的照片,例如流浪漢或毒品成癮者,結果在看流浪漢照片時,該腦區比較不活躍,彷彿這些人是物品。
哈里斯解釋,關閉這個會把流浪漢當同胞的系統,就不會有不愉快的壓力,不覺得沒施捨給這些人錢會良心不安;換言之,這些人已經某種程度被「去人性化」。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人會朝流浪漢丟酒精水球了。
去人性化是種族歧視、甚至種族屠殺的關鍵因素,而透過宣傳鼓動,可以操縱神經網路。
教育應引導本性「無分別心」
1968年,人權領袖金恩遭暗殺隔天,美國愛荷華州一個小學教師艾略特(Jane Eliot)思考該如何讓學生了解何謂偏見,她問學生是否知道被人用膚色評斷的感受,大部分學生都回答知道,但她決定做實驗來讓大家體會。她宣布,藍色眼睛的人在這間教室比較優越;棕色眼睛的人不可以直接從飲水機喝水,要用紙杯;棕色眼睛的人不可以在操場和藍色眼睛的人一起玩;棕色眼睛的人在這間教室裡要戴領圈,以便一段距離外就可以分辨。
當艾略特叫大家把課本翻到某頁時,她說:「每個人都翻到了,除了蘿莉。蘿莉,你好了嗎?」
這時有學童立刻說,「她的眼睛是棕色的」,艾略特回答,「你們會發現,我們要花很多時間等棕色眼睛的人」。
第二天,艾略特把實驗反過來,宣布棕色眼睛的人可以拿下領圈,換藍色眼睛的人戴領圈;棕色眼睛的人下課可以多5分鐘;藍色眼睛的人無論什麼時候都不准玩操場的遊樂設施,更不可以和棕色眼睛的人一起玩。
前一天一直找棕色眼睛的人麻煩的學生,到第二天感覺到深刻的失落感,之後他學會對種族主義的言論更加警惕。長大後,伊葛門採訪這位藍眼睛的學生,問他是否記得那天的行為,學生回憶說:「我對我朋友壞透了,千方百計找棕色眼睛朋友的麻煩,完全就是個小納粹的模樣,想盡辦法欺負朋友,他們幾分鐘前還跟我很要好。」
從這個簡單的實驗可知,教育可以有很大的影響力,端視教育出於哪種意圖。當我們需要設身處地理解別人立場時,就會開啟新的認知路徑。
我們希望創造一個平等的世界,更希望能達到佛陀教誨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若能深刻體認腦神經的運作機制,應該可以避免人類重演戰爭悲劇,讓生活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