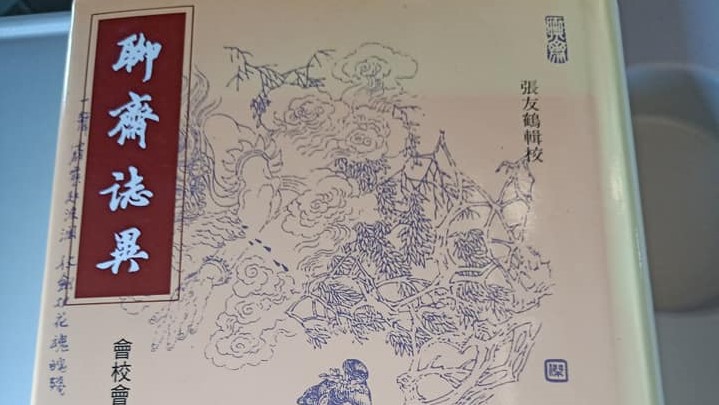<感謝蒲松齡,他愛聽秋墳鬼唱詩,我們更有理由厭煩人間語了!>
好像,這些了不起的作家,都很寂寞啊!
並且,不是普通的寂寞!
曹雪芹落魄蒜頭市場,貧病交迫,僅寫完《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的前八十回!令人驚嘆的《金瓶梅》,作者連本名都不敢示人!他會過得很得意嗎?應該不致於。蘭陵笑笑生,從此湮沒於歷史,徒留下傳聞蜚語。《聊齋誌異》蒲松齡,處境似乎在,曹雪芹與蘭陵笑笑生之間。
他沒有曹雪芹落魄。
他一生沒得意過,卻也沒有遭遇曹雪芹那樣,目睹家道中落的悲情。他比蘭陵笑笑生幸運,至少他生前,《聊齋誌異》便深受好評,雖未付梓出版,私下傳抄的份數,相當驚人!而後世,愛談人鬼狐妖,鄉野奇譚的,無人不知,蒲松齡其人其事,與其書。儘管,蒲松齡一生功名無望,他的名聲,卻早超越清朝不知凡幾的進士、舉人,而成為家喻戶曉的超級文壇明星!這些,都是他,比曹雪芹,比蘭陵笑笑生,幸運之處!
可是,人真是奇妙的動物啊。
蒲松齡原本哪裡會知道,他最終竟以《聊齋誌異》聞名天下,留名後世呢!
他十幾歲,以神童聞名,讀書過目不忘;寫文章,傲視群倫!十九歲那年,風光透頂。第一次去考「童子試」,即拿下縣、府、道,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夠嗆吧!十九歲的秀才!人人豎大拇指,按讚!大家都說,他前程似錦。但十九歲之後,考運的配額突然用完了!從此,他跨不過舉人以上的考試。他一路考到五十歲,次次落榜,落榜,落榜,落到他意氣全無!
科考這種事,不是用功,不是才氣,便保證一路順風的。考運這檔事,很邪門。你能想像,一個十九歲,科場得意的少年,之後,卻是漫長的三十餘年,從青年,中年,到初老,都一路吃鱉嗎?
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那年代,讀書人,科舉得意,跟不得意,差很大啊!得意的人,未必個個官場得意。但科場不得意,則注定官場上只能「次等人」!科場不得意者,為了謀生,要不,去替科場得意的人,當幕僚,當文書,當家庭教師;要不,自己開私塾,招學生,收學費,謀生計。
蒲松齡呢?這兩條生計,他都幹了。夠淒涼吧!
於是,蒲松齡一邊當幕僚,當老師,還一邊不斷應考。然而,他的心思,他的學識、見地,早不是科舉八股那類文體範圍所能規範的,他四十八歲時,應試再度失利,那次的經驗,是他「學問高於考試」的最好例子。他自覺考得順暢,卻因為得意疾書,嘗到「越幅被黜」(寫得太好,寫得太多,超出範圍,不算!)的懲罰!距離他最終放棄科舉的五十歲,不到兩年了。
慘吧!
但若論考場的慘,蒲松齡不算最慘!在清朝,不乏近百歲的童生,依舊想要進考場,博它一博的例子。正因為科場命運難卜,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裡,<范進中舉>後幾近痴狂的高興,才有其合情合理的背景吧!蒲松齡之所以沒有發瘋,沒有像百歲童生一樣,繼續考考考考「考到死」,跟他生命中後來有了寄託,寫《聊齋誌異》有關。
因為寫了《聊齋》,蒲松齡即便沒有舉人進士狀元的頭銜,但他的成就,他的知名度,卻遠遠超過一堆科舉得意的人!人生,什麼是得,什麼是失呢?蒲松齡寫完《聊齋》後,直到閉目,都沒看到它出版!「初亦藏於家,無力梓行」,一堆書稿,一放,要放到過世五十年之後,方得以出版!老天庇佑,一堆書稿,沒被蟲蛀,沒被丟失,沒被祝融光顧,沒被子孫賤賣!都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蒲松齡因為科場不順,始終無緣當大官。長期幕僚生涯,他當然有機會目睹官場之真面目,理解民間社會之真痛苦。《聊齋》一書,看似人鬼狐妖的傳說奇譚,然而,如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對寫實主義、理想主義兩派創作的分析:造境之人,必有所本。寫境之人,必臻理想。也就是,再怎麼馳騁的想像力,總歸有個現實的基礎連結;而再客觀寫實的手法,其作者內心亦一定有自己理想的境界。了解《聊齋誌異》,正可以用這角度去切入。
蒲松齡當然對現實世界,有諸多的感懷與不滿,才寧可投入一個理性無法解釋的,人鬼狐妖,彼此交錯的虛構世界。可是,這虛構的人鬼狐妖世界,究竟怎樣互動,怎樣失落,怎樣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呢?我們讀這些故事,之所以有感,實因「似曾相識在人間」。我們讀這些故事,之所以喟嘆,也因「答案就在此山中」。
蒲松齡是以關懷現實的角度入手,構築了一個超越現實的虛構世界,讓人鬼狐妖,重建了一些新秩序、新倫理,或者,新理想吧!他筆下人鬼狐妖,個性鮮明。他創造虛構世界,有情有義。他的生活世界有兩個,一個真實而殘酷,他必須教書為生,且不放棄登科中榜的希望(雖然越來越渺茫);另一個世界呢?不真實,但可愛。他把蒐羅來的原始故事,加以剪裁,添加他個人的詮釋、批判,當成他在真實世界裡失意的補償。
正因為他能從容出入於這兩個世界,他才沒被科場失敗打垮!也由於他在現實中的落魄,他在虛構世界裡的視野,才那麼溫暖,貼心,而感人。要理解蒲松齡的矛盾、困惑,必須從他的「兩個世界」入手。要全面讀懂《聊齋》的虛虛實實,真真假假,亦唯有穿梭於蒲松齡的「兩個世界」。
《聊齋》,是吻合「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的觀點的。只是,那些「可觀者焉」的部分,常常是在失意落魄的人身上,在狐性溫婉體貼的狐狸身上,在鬼道也有是非善惡之辨的陰魂身上!蒲松齡筆下的主角,若是人,這些人都不太得意。若是鬼,這些鬼都很可愛。若是狐,這些狐狸都很精靈。得意的人,是不需要蒲松齡特別為他們立傳的。
得意的人,也沒有什麼閒情逸致,去關心鬼狐與自己的牽扯吧?反而,是夠閒,夠百無聊賴的,有時間,有心力,去牽扯鬼狐的瓜葛。得意的儒生,「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語怪力亂神!」得意的儒生,都去當官,做大事了,誰,管鬼狐之事啊!唯有,失意人能換得清閒,在街頭巷尾,在廟口樹下,能聽得市井小民,白髮耆老們,有事沒事的閒磕牙。
蒲松齡真心相信他聽到的故事,他蒐羅來的逸聞嗎?
很難講。
從書寫上來看,他非常認真的記下,某些怪異現象的人事時地物等等細節,似乎很相信。但有時,他又會在收尾時,來上一段「異史氏曰」,有評有論,似乎又給人不過是假借這故事,啟發我們對人世的重新理解而已!
蒲松齡自己一生考場不順,他對「落魄書生」的體會,肯定極深。古代科舉,不是輕鬆事。常常是整個家族,在支撐一個有前途的年輕小夥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但這一人若不得道呢?那就慘了。《紅樓夢》裡,賈府寄託在賈寶玉和他的姪子身上。可是,別忘了,賈府雖沒落,畢竟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支撐兩個晚輩讀書,是一定夠的。
蒲松齡沒這麼好運。
他必須找工作,邊賺錢持家,邊參加科考。辛苦啊!考上,老天有眼。考不上,很合理。人家是第一志願保證班,你呢?打工回家,夜裡繼續挑燈夜戰。勵志電影可以讓你像《火戰車》,像《洛基》,一夕成名。可是,人生啊人生,沒那麼戲劇化!
蒲松齡筆下的落魄書生,為了省錢,多數住在破廟,廢棄宅邸。人煙稀少,雜草叢生,蛇狐野兔亂竄其間,怪力亂神,狐妖鬼怪,在山嵐霧氣裡滋生蔓延,都是很很合情合理的現象。這些書生,落拓已極,對鬼對狐,還有何可懼可怕呢?生命必須找一個出口。落魄之人,出口不在現世,而在光怪陸離,狐鬼交錯的迷離世界,那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啊!
《聊齋》算不算一種烏托邦境界?
《聊齋》算不算一種推開現實之窗,仰望無盡星空的冥想國度?
《聊齋》有沒有作者排遣無可奈何的愁鬱,而把美好寄託於鬼狐之杳冥的渴望?
蒲松齡是寂寞的。
還好,他排遣寂寞的方法,書寫一個杳冥的異想世界,為我們開啟了人鬼狐妖的綺麗天地!沒有《聊齋》,人間太無趣了!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延伸閱讀-
作者為知名作家
●經授權刊載,原文分享於作者臉書。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