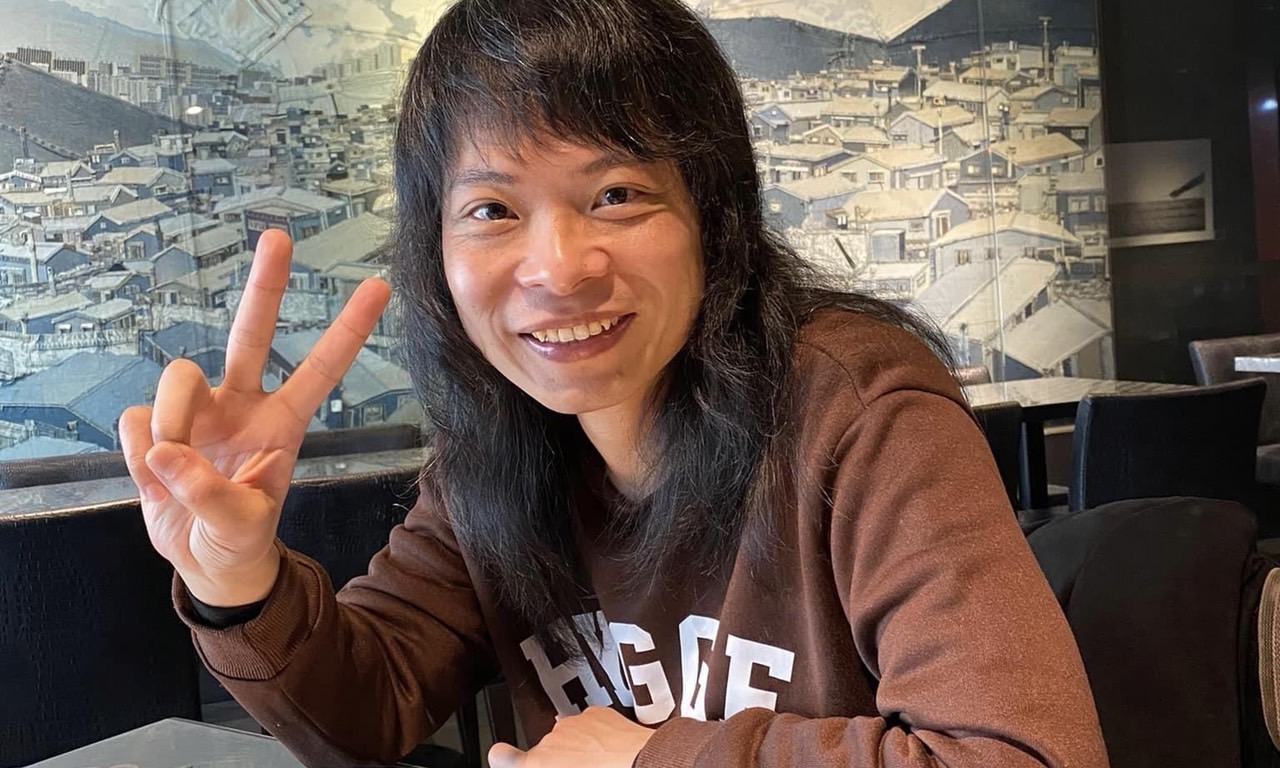【愛傳媒簡秀枝專欄】曾為電影《惡之畫》劇中的死囚犯,量身打造新作的藝術家蔡宜儒,一向以畫面張力與戲劇性取勝,更呼應電影影像的敘事性,感動觀眾。
這回中國信託舉辦的「當代繪畫獎」中,從790件參賽者中,以「美好時光之無煙硝NO.19戰役」拔得頭籌,贏得獎金80萬元,擠身該集團典藏藝術家之林,再次受到矚目。
今年40歲蔡宜儒,從早期黑白水墨,到中後期的作品,如《搖滾童話》、《叢林派對》等,夾雜動物的赤子之心、高彩度的濃烈情緒,繪畫脈絡清晰,擅長把殘酷的現實,轉化為畫布上的童趣想像,作品張力十足,帶著戲劇效果的敍事性,相當耐人尋味。
3月3日一大早,還頂著狀元桂冠的蔡宜儒,出現在《典藏-長安咖啡店》,長髮及肩,像個當代樂手,他點了土司煎蛋黑咖啡,一邊大口享用他的早餐,一邊暢談他的創作歷程。
「我從小就喜歡畫畫,不畫,好像遊魂野鬼,頓失生活重心!」蔡宜儒話夾子一開,就是藝術創作,靦腆靑澀的表情,有股執著藝術的霸氣。
他在電影《惡之畫》化身為隨機殺人犯背後的藝術槍手,隨機殺人的邪惡性,與藝術真善美,恰是兩個極端,藉由死囚的畫作,帶出藝術作品與創作者人格之間的道德爭辯,還有藝術純粹性的嚴肅問題。最後大家不禁要問,人性中是否隱藏著「不同程度之惡」的表現!?
曾獲金馬獎最佳美術設計的李天爵,擔任電影《惡之畫》的藝術指導,為貫穿全片的畫作,他找到氣味相符、靈魂相投的藝術家蔡宜儒為角色量身打造獨一無二的畫作。相當難得的是,藝術作品首度擺脫配角,成為電影靈魂之一,從他們合力在劇中訂製藝術家,引入藝術家的創作靈魂,讓畫作在片中跳脫單純的美術道具,成為擁有精神、具生命力的「角色」之一。這種以戲劇文本為骨幹,建構獨特視覺美學,讓角色情感,完全投射融入場景之中,展現獨特的電影層次。
抖落電影中善惡角色,回歸現實面,蔡宜儒從人類受疫情蔓延影響,找到創作的嶄新切入點,果然一舉奪冠。曾被網路形容是「台灣視覺藝術的搖滾詩人」,蔡宜儒認為,帽子扣得太大,敬謝不敏,他希望保持靈活性,繼續探索未知領域。
1980年出生的蔡宜儒,是台北人,早期台北後火車站的巷弄中,有許多違建鐵皮屋,住了許多討生活的底層百姓。蔡宜儒父親蔡明璜、母親陳照真,就在那樣的環境裡,以打鐵焊接的粗活為生,居家即工廠,白天打鐵時,火花四射,噪音喧天。
父親在正廳幹著燠熱粗活,母親打理工人三餐,因為打鐵噪音太大,和工人對話時,或有電話要轉接,她屢屢以擴音喇叭傳送訊息,簡直是魔音傳腦。夜晚,大人會三二坐在巷子隅角,喝點老酒聊天,工作雖然辛苦,但他們彷佛看到社會在改變,向上揚升的希望,各個樂觀看待。
蔡宜儒與小他5歲的妹妹蔡羽彤,非常認命,乖乖的上下學,自己玩,不吵忙碌幹活的父母。尤其愛畫畫的蔡宜儒,到處塗鴉。反正工廠客廳已經髒亂,父母也不會阻擋他在牆上亂畫,孩子不吵,做什麼都好,那樣的吵雜環境,反而孕育了蔡宜儒的生猛活力。
工人做記號用的彩色粉筆、三伯油漆店用剩的原料,舅舅印刷工廠裁切後的紙頭,都成為他捶手可得的畫畫工具,所以,在蔡宜儒的認知中,他是豐盈幸福的。
蓬萊國小、建成國中,一直到中正高中普通班,畫畫都只是他個人好玩的課餘消遣而已。位於士林的中正高中,校園十分遼闊,但教官管理嚴格,熱衷於抓髮禁。但蔡宜儒發現,在校園在藝德樓,卻有一群學生,可以留長頭髮。他好奇去打探,原來是舞蹈資優生,需要飄逸長髮好打扮,讓他非常訝異與羡慕。
有為者亦若是,愛畫畫的蔡宜儒,多麼渴望自己也能進入美術培育殿堂。他找到火車站附近,專門輔導美術班學生的「陳嘉仁畫室」,學習正規美術基礎教育,畫素描、水彩與國畫,密集上課,讓他從草莽塗鴉,邁向正規學習。
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蔡宜儒順利考上嘉義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系,他十分開心,總算踩進藝術之門。大三開始分科別,他喜歡書畫的筆墨趣味,特別是書畫的文學性,他成績出色,一路領先同儕,甚至不惜以不同畫風,幫同學代筆繳交作業,因此讓他體驗多元畫風的創作形態。
大學畢業,又考進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創作組,研究所畢業後,曾短暫到畫室代課,但一切都不如他閉門創作來得開心,最後辭掉所有工作,選擇過著節衣縮食,專心創作的清苦生活。2012 曾到日本常滑市當駐村藝術家,2015年又到韓國Daedam美術館駐館藝術家 ,啟發視野,更練就一身好功夫,希望能在當代創作領域,大展鴻圖。
不過,也有失落感的時刻,有回老同學開著新轎車向他獻寶,大燈對著他的畫室照射,讓他嚇了一大跳,情緒頓時陷入低潮。同學在外打拼有成,車子房子逐一落實,而他還是在顏料堆裡攪和,茫茫前途無所寄,畫筆一度畫不出東西來。然而,幾經思量,他還是說服自己,回到孤獨畫室,守護孤筆畫布,他重新期待以五彩顏料,打造他的繽紛夢想與未來。
蔡宜儒非常感謝他的家人,始終給他完全的自由與信任,父母親都不懂藝術,見面時還都是問著「有吃飽穿暖」的家常話,不曾埋怨他的閉關宅男生活,以及不穩定的收入現況。而世新廣電系畢業的妹妹,也是心存體諒,滿溢的噓寒問暖,讓他倍感溫馨。
由於在大學主修過水墨書畫,蔡宜儒不同於時下年輕藝術家,只沈醉觀念,不重基本功。他時時以東方水墨底蘊,作為繪畫創作上的發展根基,在保留傳統皴、擦、點、染等筆墨精神之餘,也融合了西方現代繪畫表現裡的造型思考元素,進而從作品中,得以閱讀一股有別於傳統書畫的赤子童心、幽默意趣與個性化的總體表現,而從整個視覺風貌的建構來看,不難發現其作品,包融了東方與西方,整合了抽象與具象之間的微妙特質。
蔡宜儒在創作執行面上,先用水性壓克力顏料表現整體,同時增加塗、刷、抹、刮等更直接的手法,面對畫布的當下,他回歸本能性的大動作揮灑,從破壞畫面來建構新可能性,種種動態表現呼應起野獸復甦吶喊的主題精神。
蔡宜儒曾在《搖滾童話》中自述,走在創作的路途上,與其把心放在未知的未來,不如將心安在創作上的初衷,走的越遠,反而越是感到初心的珍貴。於是,回溯著年幼時的塗鴉記憶,還有他在孩童時期常畫的戰車、恐龍,甚或一些非現實世界的物種等等,那些熟悉的影子,陸續在腦海中浮現。
童年回憶,召喚了他的赤子之情,一時之間,創思泉湧,他透過彩筆,重新建構起異想世界中的童話丰采,找到初心的喜悅,他精神為之抖擻,心靈中,最柔軟、舒坦與誠摯的部分,讓他心思飽滿了起來,自由表現的勁道再起。
搖滾,是一種存藏內心的種苗,也是他繪畫骨子裡的基因,生命的熱力激情,盡在其中,搖滾童話,果然熱力四射。講起話來溫文儒雅的蔡宜儒,對照他帶有童趣,但又展現嘶啞怒吼的畫作,讓外界看到其中的落差。蔡宜儒以誠實作畫,自我解嘲,他說,藉由創作,釋放他內在的熱氣,那是展現他內心深處中的狂野與草莽性,真誠直白,力透畫背。
這回參與中國信託舉辦的「當代繪畫獎」,好像有幾分神助,他心頭喜孜孜的。蔡宜儒解釋,約莫從2020年至今,肉眼看不見的COVID-19病毒,以超乎想像的速度瀰漫全球,疫情改變了原本的生活方式,眼前的人類,彷彿歷經了整個地球的重整,正在過渡期之中,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都為未來的不確定性,惶惶不安,身為藝術創作者,他更能感同身受。
蔡宜儒以人文關懷的視角,回應疫情當下的內心波折,並作為創作發想的核心基調,而在作品造型的傳達上,他回歸童心、回溯過往記憶,用陳年往事的角度取材,讓整體作品立基在「以昨日的角色,來演述今日的故事」軸線上,做了發展與延伸。
「如果說 ,記不得的從前,自然成為過去,而忘不了的曾經,終將成為回憶。」蔡宜儒信誓旦旦。
果然,蔡宜儒在作品鎖定了他兒時回憶中,未曾忘懷的卡通人物、模型等要素,例如,小叮噹、哆啦A夢,穿梭過去與未來,解決各式難題的超現實角色,頗能作為象徵實現夢想的大神。在迪士尼的世界裡,不論多麼頑劣的暴風雨,到最後總能撥雲見日,象徵了歡笑、希望與夢想的實現,非米老鼠、唐老鴨莫屬。
在人與人因實體距離,被迫拉開的日子裡,透過通訊貼圖,維繫日常人際的表情象徵的通訊軟體貼圖,也在天災人禍的日子裡,居功厥偉。為愛出征,對抗這場因病毒而起的無煙硝戰役愛心手指坦克模型,也擔綱挑了災難歲月的大樑。
蔡宜儒強調,那些在兒童時代陪伴成長的圖像角色們,仍舊像一顆顆鮮活的種子,植藏於記憶沃土中,等待著透過創作,讓它再次開枝散葉。
於是他挺身召喚昔日的偶像,擔任起創作要角,熟悉圖像,呈現出的懷舊情愫,與他自己在成長經驗中的共感印象,試圖連結出觀者的共鳴,也透過記憶拼貼與多重視點的概念,把記憶中的圖像,鋪排於畫面上,輔以繪畫性手法,重新組構,連結起口罩、疫苗注射等符號,整體畫面,彷彿在東方筆墨意趣氛圍的文化背景裡,有了因應主題的多層次想像,因而在畫面上,營造出歡愉、幽默、童趣十足的視覺感受,反喻了人類面對無常現實世界時,內心所感受到的荒謬性與無力感。
當作品外顯的繪畫表現性,與內在蘊含的關懷視點,經由反差筆調,交互應用,加深印象,就成了該作品所命題的「美好時光之無煙硝NO.19戰役」,言簡意賅,發人深省。
從創作年齡來說,蔡宜儒是台灣當代藝術界近年鵠起的新秀,畫面上有筆墨線條的功力,卻又能在壓克力顏料的經營上,鏗鏘有力,卓然有成,也備受期待。
蔡宜儒帶著感嘆口吻說,繪畫創作彷彿是一道可以暫時忘卻時間的好方法,走筆的痕跡,順著無聲的時光之流,在畫布前,未曾止歇,轉眼間也悄悄地進入了不惑之年。他有感時光向前推進的同時,也將與自身過往回憶的厚度成正比,於是朝往童年回溯的角度漸漸成為他近年的創作視點。
蔡宜儒在兒時自發性常畫的飛機、恐龍、戰車等元素,在先前2019年「搖滾童話」個展中已登場過,而近期他順著當年記憶溯源,繼續推想,並鎖定了兒時回憶中難以忘懷的卡通、電玩人物,以揉合西方造型思考與部分東方筆墨意趣的繪畫性表現,讓角色伴隨著想像,與馳騁的筆調,一同悠遊古今,希望在舊時光的共感情愫中,營造出另番鮮活的樂趣與況味。
「以昨日的角色來演述今日的故事」,蔡宜儒藉由歡樂幽默的童趣筆調來反芻面對現實世界時內心所感的荒謬,同時也寄望在保有初心的視角下,對於詭譎未來,依然持抱美善的遙望。
古人將筆墨寄情在前人詩詞山水文本間,得以抒懷,如今遁入過往時光中,重新取材造境,同得類似可行、可望、可遊、可居之樂,蔡宜儒胸有成竹。
「如果我們說回溯是一種將人生走過的前言與後記,重新鋪寫出新曲的方式,看似回頭,卻又不失為是一種再向前行的開始,那麼筆尖逆鋒指向後照鏡裡的來時路,或許將會是漫漫創作旅途上再次整合後的新起始!」蔡宜儒信心滿滿,樂觀開朗面對未來。
作者為典藏雜誌社社長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更多文章見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