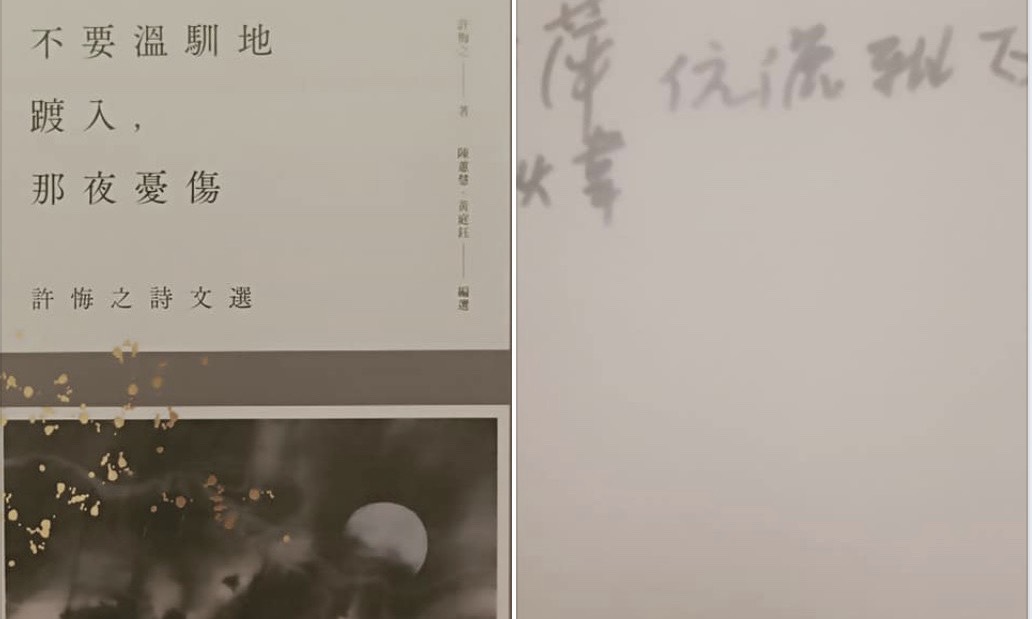〈為許悔之的《不要溫馴地踱入,那夜憂傷》詩文集而作〉
寫完張愛玲系列,突然有鬆一口氣的喘息感。眼角立刻掃描到,放在桌邊的詩集,許悔之的,《不要溫馴的踱入,那夜憂傷》。準確講,應該是許悔之的詩文集。而且是出道三十年的典藏紀念版。
我望著封面上,選的水墨作品,局部的〈水中之月〉,在抽象式的水墨氤氳中,我的心思飄到很遠,很遠以前。悔之都出道當詩人,當文字的精煉師,超過三十年了嗎?也就是說,我翻著這部選集,等於重溫過去三十年至今的,悔之的創作之路呢!
那詩句,飄逸著人生稚嫩的渴望,如〈絕版〉:「如今/風翻看的每一頁/都不可圈點/是孤本,且永遠絕版」如〈共傘〉:「雨停後整個世界輕輕咳嗽,我們抬頭/仰望一柄好大好大,明明滅滅的我們的傘⋯⋯」
一如人生的青春期,浪漫,雀躍,容易感傷,但純潔到令人感動。但,生命並不如夢,我們經歷的一切也不是夢,於是,詩人的詩句也在歲月裡煎熬了。
詩人知道,他的句子也知道,生命是煎熬。
〈我的強迫症〉:「我不斷的撥打電話/撥給來世/撥給前生/撥給今生的你」
我格外喜歡〈奔跑〉。
「我一直奔跑一直/奔跑奔跑/在你的一個毛孔裡/像一隻銀狐/在廣袤的雪地上/奔跑/在感覺你胸悶之時/你,一定有悲傷吧/我以為那時宇宙正在崩解/而忍不住停下來/仰天嗥叫」
往事並不如煙。我們又是記憶的動物,詩人怎麼能不靠刻意的強迫症,逼使自己正對人生的陰暗,或明亮呢!認識悔之,也應該超過三十年了。陸續讀他的詩,聽他說話,看他蹙起眉頭,望著他走開的背影。
詩人,總有一塊糾結的心。我不容易懂。但知道那是詩人之所以為詩人的特權。但我總希望,他應該再眉宇陽光一些。文字表露出的心底,難免有文字的遮蔽效果,宛如冰山一角,你只能憑藉表露的部分去推測隱匿的部分。
悔之習字、畫畫之後,眉宇間寬闊許多。那些在文字裡壓抑的感情,在宣紙上,顯然抑揚頓挫得厲害。在水墨的佈局中,我看到一位詩人不曾有過的昂揚。也許,他本質上,就該是一位藝術家的。
我跟悔之都是畫家于彭的朋友。于彭走了之後,悔之寫了首詩,已經透露了他即將發生的的心事。
「一座山是墨/大地是硯/千年的靈樁是筆/你揮筆/筆補造化/寒露凝結於/一切花瓣葉尖/宛若來不及滴下的淚/冰魄水魂/俱都黯然凝結了/是不應該悲傷的/我獨立在你的畫之前/巨大而自由的風/從宇宙吹來/宇宙並不掉下眼淚」
宇宙並不掉下眼淚。
一九六零年代,張愛玲描述於紐約看到胡適,見他失去自己的土壤,流寓海外的孤寂時,她用了「一股歷史的冷風颼颼從遠方吹來」做隱喻,寫出了胡適的蒼涼。
但于彭不是,他生機勃勃,在自己的土地上,很有使命感的為當代水墨尋求生機。他的英年早逝,固然有朋友的不捨,然而,也因為是朋友,悔之看到了藝術家的揮灑之間,寬闊如風的自由!
其實,悔之何嘗是看到好友于彭的殞落背後,獻身水墨創新的歡愉,他也應該是預見了自己,在詩,在書法,在水墨之間的新的意象的翻起跌宕,那是真正的人文意識的勇敢!
不要溫馴地踱入,踱入那夜的憂傷。
既然如此,就一起在夜之漫長中,點一盞詩人的燈,燃一把藝術的火炬,在雪原上迷路,在浪花上嘶鳴,在月光下顫抖,在我們所遺傳自的創作的基因裡,在人生最痛的地方,打開最遼闊的海。
我們別無珍貴之物,除了詩,除了文字,除了躍動的靈魂。但還好,悔之,你還多了水墨暈染的一片天地,你還知道宇宙不掉淚!
作者為知名作家
●經授權刊載,原文分享於作者臉書。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